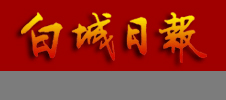敦煌莫高窟第23窟有一幅“雨中耕作图”,画面上乌云密布,时雨普降,一农夫挥鞭策牛,雨中耕作。敦煌千佛洞也有一幅玄奘取经图“水月观音变”,画面上明月高照,彩云环绕,绿水扬波,观音坐在金刚宝座上,玄奘双手合十向观音膜拜,猴行者牵着白马紧随其后。这些画面对于今天年降水量仅40毫米、蒸发量却在2400毫米的敦煌来说,是不可想象的。以佛教壁画形式把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了的理想揭示出来,这也反映了干旱地区居民内心对水的渴望和被环境折磨挣扎的人生。
如今的现实远没有想象那般苦,今天的敦煌城,俨然一座现代化的旅游城市。下飞机之后,却有一种天干物燥的感觉扑面而来,空气仿佛被抽干了水分,汽车在柏油路上飞驰,路两边都是同样的风景——戈壁荒漠。一种无言的凄凉与寂寞不可阻挡地袭上心头,一切的大辉煌尚在背后,缺水的现实已经逼在眼前。
那么,敦煌因何而兴呢?答案让人惊讶,是水,缺水的敦煌因水而兴。明代《沙州卫志》记载:“敦煌雪山为城,青海为池,鸣沙为环,党河为带;前阳关后玉门,控伊西制漠北,全陕之咽喉,极边之锁钥”。
敦煌面积不过3.12万平方公里,绿洲面积不到5%,其余均是大漠孤烟,长河落日的茫茫戈壁沙漠。然而,如果身处视线无阻之地,你就能远眺到连绵1000多公里的祁连雪山。海拔4000多米以上的山峰,终年积雪,形成了硕长宽阔的3000多条冰川,每年融化雪水数十亿立方米,有的潜入地下,到山前低地露出,形成泉水;有的流入低洼地带,形成江河湖泊,在河西走廊形成50多条大小河流。
正是祁连山冰川融化下来的水,才形成了敦煌这块水草丰茂的绿洲,成为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;又逐渐形成了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军事重镇,商旅大埠,佛教圣地,也造就了莫高窟这个伟大的艺术宫殿。
莫高窟位于敦煌城东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,据资料记载,在距今2.85亿年的古生代二叠纪以前,这里是一片浩瀚的大海,大约250万年山前盆地缓慢上升和水流冲刷,形成一条长1680米,高10——45米的崖壁。于是1600多年前,乐尊和尚以此开凿第一洞佛窟,由此展开了敦煌的辉煌。
可以说敦煌兴之于水,只不过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,如今的敦煌被包围在茫茫戈壁沙漠之中。近十几年来,日益枯竭的地下水源和不断东进的库木塔格沙漠,让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生存之地显得生态环境形势特别严峻。
据说敦煌的母亲河党河,每年从祁连山上融雪而形成的水流量近3亿立方米,被每年的农业灌溉就用得一干二净。50多年前,党河还有上游的疏勒河来水,上世纪60年代,疏勒河上游建了2个水库,疏勒河遂断流。后来敦煌只能靠抽取地下水弥补用水缺口,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,1975——2001年,地下水位下降10.77米,并且现在仍以每年0.24米的速度持续下降。水源严重短缺和地下水位下降,使敦煌市原有的1万多亩的淡水湖80%的面积已不复存在,目前全市仅存天然林130万亩,草场31万亩,湿地270万亩。自1994年以来,敦煌绿洲外围沙化面积增加了近20万亩。
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现实是,自汉代即为“敦煌八景”之一的月牙泉,数千年来身陷流沙不被淹没,没有水位下降的历史记录。然而,近30年来水位竟然持续下降,由上世纪的1.45万平方米、水深7.5米,萎缩到今天的7476平方米,水深1.3米。本是“沙水共生”的奇景,如今也只能靠抽取地下水补充来维持了,成为大敦煌荒漠化、沙漠化最典型的见证。那么,敦煌人乃至中国人还不应该警醒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