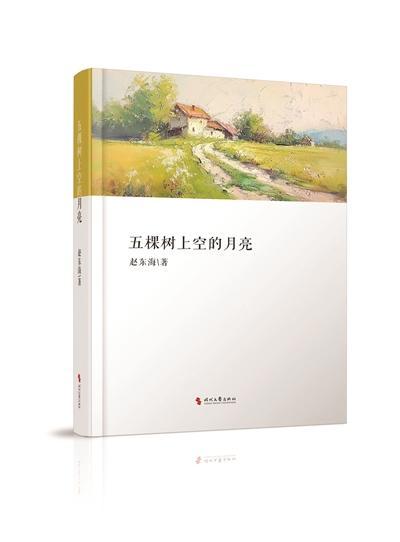●刘焱
赵东海的散文集《五棵树上空的月亮》以白城镇赉五棵树村为地理坐标,在东北方言的韵律与自然意象的层叠中,构建了一座连接乡土记忆与城市回望的文学桥梁。这部作品不仅是乡愁文学的“穿越表达”,更在方言语料、自然意象群与时代精神的交织中,呈现出东北乡土文学的独特美学价值。
方言叙事:
乡音的肌理与情感的温度
在作者的笔下,东北方言词汇运用比比皆是,比如“那嘎达”“干啥”“咋的”等,这些并非简单的语言点缀,而是作为情感密码与地域身份的标识,嵌入叙事的肌理。这种方言的“在地性”与城市视角的“疏离感”形成张力——当作者以移居者的身份回望故土时,方言成为唤醒记忆的钥匙,既重构了童年场景的鲜活,又凸显了城乡文化碰撞中的身份焦虑。正如《北京文学》评语中对语言“讲究”与“结构精巧”的强调,作者将方言的粗粝感转化为文本的呼吸节奏,让乡愁在语言的褶皱中自然流淌。
自然意象:
原生态美学的符号系统
散文集中反复出现的“五棵树”“田野大院”“野草”“公鸡”“花猫”等意象,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乡土符号系统。这些意象既承载着东北地域的自然特征(如“五棵树”作为地标的历史沉淀),又通过拟人化书写被赋予情感重量——例如“花猫蜷在磨盘上打盹”的场景,既是乡村日常的切片,又暗喻时光停滞的永恒性。这种“草木有灵”的书写策略,与《山中芝兰》对云南山村“草木淡雅幽香”的象征性处理异曲同工,但赵东海更强调意象的“功能性”:果树见证家族繁衍,野草隐喻顽强的生命力,公鸡啼鸣则成为乡村时间秩序的标尺。这些意象群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逝,因而其书写本身便构成一种文化抢救。
时空交错:
乡愁的双重维度
作者以“城市长大的人”视角展开叙事,形成双重时空的交错:一方面,童年记忆中的乡村是“未被规训的原生态乌托邦”,如《父亲的马》中幻想之马对自由的隐喻;另一方面,现实中的乡土在现代化冲击下面目模糊,成为“回不去的田野”。这种张力在《五棵树上空的月亮》中体现为月光意象的变奏——记忆中的月亮“悬在五棵树梢头,照着谷垛和萤火虫”,而今却“被高楼切割成碎片”。这种时空对比,恰如万玛才旦小说中“传统规矩与法律冲突”的现代性困境,但作者通过诗性语言将矛盾升华为美学沉思,使乡愁超越个人怀旧,指向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碰撞的集体记忆。
乡土文学的内在价值:
从地域性到普世性
该散文集的深层价值,基于将东北方言与地域经验转化为人类共通的情感结构。作品中“深沉的时代精神”并非直白的社会批判,而是隐匿于细节:如“野草从砖缝里钻出”暗喻乡土生命力的顽强,“乡间大院门楣褪色”见证家族伦理的变迁。这种“以小见大”的叙事策略,与《高原的“野牦牛”》通过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图景的路径相通,但赵东海更注重日常生活的神性挖掘——在《牧风人》等篇目里,放羊老汉的烟袋、母亲的酱缸都成为文化基因的载体。这种书写使东北乡土文学突破地域局限,成为当代中国城乡转型的微观史诗。
结语:
散文集《五棵树上空的月亮》以方言为舟楫,以自然意象为航标,在个人记忆与集体经验的河流中溯游。它既是对东北乡土美学的深情重构,也为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失语症提供了疗愈方案。这类创作打开了本土作者作品走向读者的广阔天地,而其更大的启示在于:乡愁不应仅是怀旧的挽歌,更可以成为重审现代性、重建精神家园的叙事方法。当五棵树的月光照进城市读者的窗口,那些被方言点亮的记忆碎片,终将在文学中凝结为永恒的乡愁晶体。
作者简介:
刘焱,白城市作家协会会员、援疆教师。